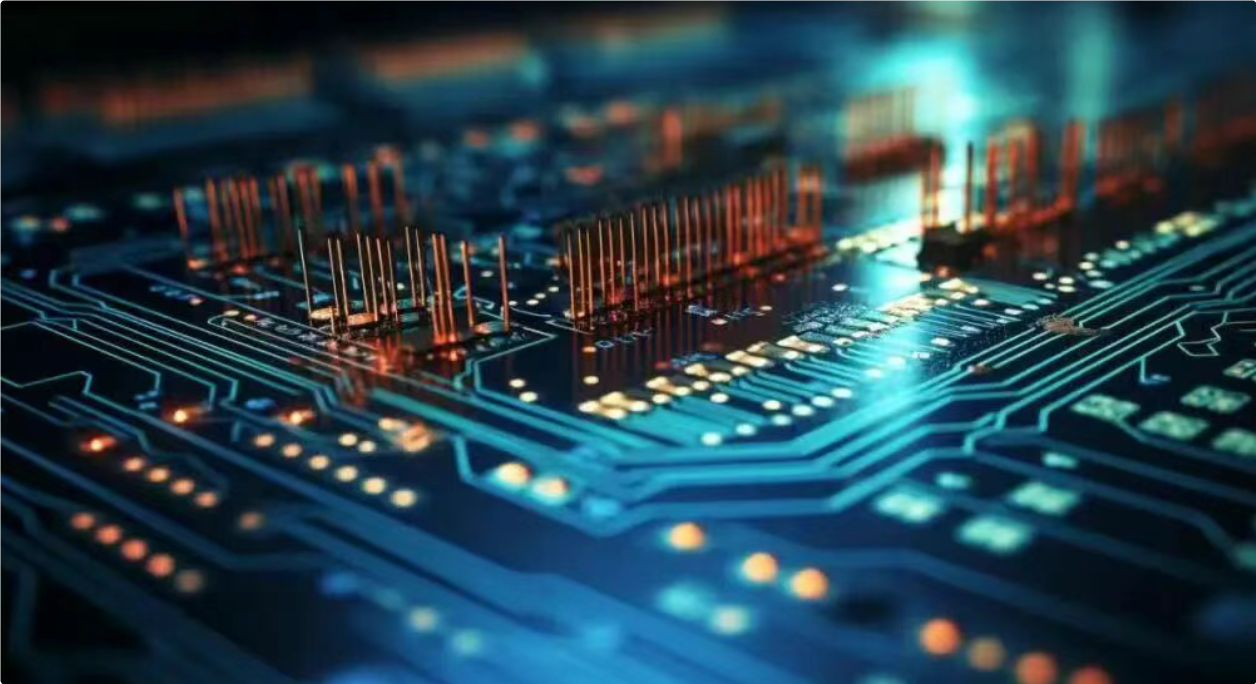中美博弈之下,可怜的AI创业者们

前几天看到 Manus 创始人肖弘的那条社交媒体动态,心里很不是滋味:今天仍旧在 AI 的早期,为了让更多人用上而放弃短期的收入,甚至调整商业模式的,都是一件可以被做的事情。
想要在全球化的市场里做好产品,有很多不是来自业务本身和用户价值本身的烦恼,偶尔也会想起上大学时的偶像发饭否的那句话,「多少艰苦不可告人」。
但这一切是值得的。一方面因为旅程本身就有很多开心的、让自己和团队成长的事情。另外一方面,如果最后有不错的结果,证明作为中国出生的创始人,也能在新的环境下做好全球化的产品,那就太好了!
提到那些“不是来自业务本身和用户价值的烦恼”,最后那句“证明作为中国出生的创始人也能在新的环境下做好全球化产品”,像一根细针,扎中了当下AI创业者的集体心事。
最近很多人在讨论 Manus 业务调整、疑似退出中国市场的事,具体细节大家可以去查相关报道,我不多说。
我也是纠结了很久要不要聊这个话题,它太敏感了,但思来想去还是想收着说几句,我的结论也很明确:这一代中国 AI 创业者,是被夹在大国博弈裂痕里的特殊群体,他们脚下的路又窄又滑,想转身都难。
因为,AI 领域的“楚河汉界”已现。要明白处境,得先看清一个大前提:中美在 AI 领域的“割裂”已成为事实。现在想在 AI 行业创业,从第一天起就面临一个绕不开的问题——“选边站”。
大模型就像一个超级大脑,通过学习海量数据形成对世界的认知,而应用则是把这个大脑的能力拆解、包装,变成普通人能用的工具。
打个比方,大模型是电厂,AI 应用是电器,电厂的电压、接口标准决定了电器能在哪里用。
中国的大模型如DeepSeek、Qwen,美国的ChatGPT、Gemini,就像两套不同标准的电力系统,用谁家的电,就得按谁家的标准造电器。
这种技术标准的差异,本质上是数据训练和合规要求的产物。
中国大模型的训练数据里,中文语料、国内法律法规、社会文化常识占比极高,生成内容时会自动规避敏感信息;美国大模型则基于全球多语言数据训练,更擅长处理复杂逻辑推理,但生成内容的尺度受西方价值观影响。
这就导致一个现实:用美国大模型开发的应用,很难完全符合中国的内容监管要求;用中国大模型做的产品,在海外市场可能因为文化适配性不足而遇冷。
我认识一位做 AI 法律咨询工具的创业者,他的团队最初想做一款能同时服务中美企业的产品,帮用户自动生成合同初稿。
但实际测试时发现,用GPT-4生成的美国合同模板里,有很多条款涉及对中国市场的限制性表述,在国内根本无法使用;换成国产大模型后,生成的英文合同又因不符合纽约州的法律条文规范,被海外客户退回来。
最后团队只能拆分研发,分别基于两套大模型开发产品,人力成本直接翻倍。这就是技术割裂带来的直接代价——本可以集中精力打磨核心体验,却不得不把资源消耗在无意义的“适配”上。
但技术只是第一道坎,市场、资本的割裂让选择更残酷。
现在的AI创业者,从起步就要在三个维度做“单选题”,而且这三道题的答案必须一致,否则就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。
市场割裂的直接后果是“双向不可达”。中国用户想用ChatGPT的高级功能,得翻墙上特殊网站,还可能面临账号被封的风险;美国用户想试试国内的AI绘画工具,要么注册不了,要么生成的内容不符合他们的审美预期。
创业者如果想兼顾两边,就得做两套完全不同的产品:界面设计、功能侧重、运营策略全要分开,这对初创公司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。
另外我接触的一家做AI社交工具的团队,他们最初想做一款能帮用户自动生成跨文化社交话术的产品,比如帮中国人写英文邮件、帮美国人理解中文的寒暄礼仪。
但运营半年后发现,国内用户觉得产品“不够实用”——他们更需要的是帮写工作总结、生成短视频文案;海外用户则觉得功能“太繁琐”——他们只想要简单直接的翻译工具。最后团队不得不砍掉一半功能,专注服务国内市场,海外业务不了了之。
有位创业者同行跟我吐槽,他的公司A轮融资时同时接触了国内一家产业基金和美国一家风投。
国内基金要求他承诺“核心技术不向海外转让”,美国风投则提出“必须把研发中心搬到硅谷”。这两个条件根本无法同时满足,最后他选了国内资本,代价是海外市场拓展计划被迫搁置。“不是不想出海,是拿了国内的钱,就被捆住了手脚。”他说这句话时的无奈,我记得很清楚。
这三重割裂像三个同心圆,创业者必须站在某个圆里,跨圆行走的代价是轻则业务受阻,重则公司停摆。
所以肖弘才会说“有很多不是来自业务本身的烦恼”——他们要花大量时间研究出口管制清单、数据跨境规则、资本审查条款,这些精力本可以用在优化产品上,而且这一类事情耗费时间、金钱和精力。
欧洲、东南亚、拉美这些地区的AI渗透率还很低,对实用工具的需求旺盛,这本该是中国创业者的机会。
只不过现实没那么简单。这些市场看似中立,实则深受中美博弈影响。
欧洲有自己的 AI 法案,对数据隐私的要求比美国还严,且在技术标准上更倾向于跟随美国;东南亚国家大多是美国的盟友,对中国AI产品既想用又提防,常常以“安全审查”为由设置壁垒;拉美市场则受美国技术霸权影响,核心基础设施依赖美国云服务,中国AI应用想落地就得适配美国的技术生态。
“夹缝中的创新”正在成为常态。
我身边一位朋友和我分享总结出一套“生存法则”:用国产大模型开发核心功能,针对海外市场做“去敏感化”处理——比如去掉涉及政治、宗教的模块;拿中东、东南亚的资本,避开中美资金的限制;先从对技术来源不敏感的行业切入,比如餐饮、零售这些轻工业场景。
这些方法听起来很“憋屈”,却是当下能走通的少数路径。
肖弘说“如果最后有不错的结果,证明中国出生的创始人也能做好全球化产品”,这句话我理解,是我们这代创业者的集体执念。
我们不想只做“中国的AI公司”,更想做“来自中国的AI公司”,但这条路被大国博弈的阴影笼罩,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。
观察这些AI创业者的挣扎,我自己也有几点很深的体会,不仅适用于AI行业,也适用于这个时代的很多领域,做个分享:
美国对TikTok的审查,本质是本土科技公司对竞争的抵制;中国对数据安全的重视,源于对国家主权的维护。理解这些背后的逻辑,才能找到安全的生存空间。
这种对现实的敬畏,反而让他们在多个国家打开了市场。
最后总结一下:不管遇见什么事情,总是要在裂缝中生长的力量。
没办法,我们这代中国 AI 创业者确实可怜,赶上了 AI 技术爆发的好时代,却也撞上了大国博弈的坏时机。
我们的才华本应用在突破技术瓶颈上,却不得不消耗在应对非业务挑战上;我们的视野本可以放眼全球,却被无形的墙限制了脚步。
但换个角度看,我们也是幸运的。这种在裂缝中求生存的经历,会让我们比前辈更懂得全球化的本质——不是技术的无边界流动,而是不同文明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协作。
或许正是这些艰难,能催生出真正有韧性的全球化企业。
肖弘说“多少艰苦不可告人”,但他后面紧跟着“这一切是值得的”。这种在困境中的坚持,或许就是我们这代创业者最珍贵的品质。
我们就像在石缝里生长的树,虽然长得慢、长得歪,但根扎得深,总有一天能把裂缝撑成属于自己的天空。
我相信,当若干年后回望这个时代,会有人会记得这些在中美博弈中艰难穿行的AI创业者们。我们的挣扎与坚持,不仅书写了自己的故事,或许更在不经意间,为技术与文明的对话探索着可能的路径。
作者:稳德亮,红熊AI
© 版权声明
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,未经允许请勿转载。
相关文章

暂无评论...